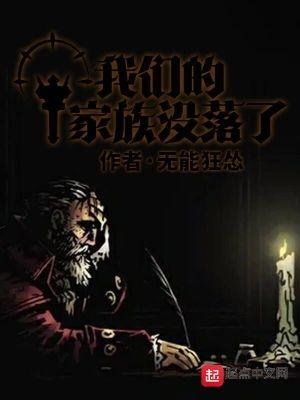笔尖小说网>盐祸猪六戒 > 2030(第13页)
2030(第13页)
陈脊‘呀’的惊呼出声,“我想起来了,我曾在本地县志中看过,那场大火烧了整整一夜,三十四名僧侣遇难,着实是件惨死。”
沈亭山闻言静默了许久,眉头却越拧越深。良久,复开口道:“梁叔,黄柳生其人你可了解?”
“我对他所知不多,当年他可还不像今日这般负有盛名。”
“怎么回事?”
“当年两淮两浙的航道虽也有私盐贩子为恶,不过大多是些散兵游勇,成不了气候。八年前,黄柳生也就是这些散兵游勇中的一员。我没记错的话,他出身灶户,会些拳脚功夫,因受不了盐场的苛待,才领了几个盐丁反了。”
沈亭山问:“您的意思是说,八年前劫船案发时,他的实力并不雄厚?”
梁宽点了点头,又长叹了一口气道:“我当时若知道黄柳生是这般凶残的人物,定不会放着那十五个手无寸铁的兄弟去白白送死。”
“梁叔,我再与你确认一遍。当年的黄柳生实力并不雄厚,那他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劫杀一艘载有三十几人的官家盐船?据我所知,尹世昌的功夫手段在两浙也是出了名的。”
梁宽一怔,道:“这这我倒是没有想过。如此说来,当年之事确有古怪。”
“梁叔你再仔细回想一下,看是否还有什么遗漏的细节?”
“细节”梁宽低着头,手中佛珠快速转动,沉思良久后,道:“尹世昌出海那日,曾提到一个人,姓夏。”
“夏?”
“我问他这官盐船是从何处运来,竟走了这许多时日。他叫我莫要多问,总归姓夏的不会亏待大家。还有,他那日心情异常的好。”
“异常的好?”
“尹世昌那段时间家中遇到难事,终日脸上难见笑容。可那日来见我时,却笑脸盈盈的,仿佛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在等着他。”
陈脊好奇地问:“是何难事?”
“这我倒不曾打听。左不过是家中有人生病亦或是在钱上一时难住。成家之人,又有衙门口的活计谋生,能难住他的也就这两件事了。”
沈亭山沉吟片刻,暗想:“朝中姓夏的大臣有父亲的恩师夏言,夏伯伯。他的亲族势力倒是盘根错节。”思及此处,他又不免想起李永安和郑劼来,“郭槐与夏伯伯在朝中争锋相对,郑劼又是郭槐的侄儿,不知这其中是否有所关联。”
沈亭山想着又笑着摇了摇头,试图驱散这个荒谬的想法。“夏伯伯一生高风亮节又远在京城,怎么会与这山阴的命案牵扯到一块呢?朝中姓夏的大臣并非少数,我不如晚些时候修书一封给父亲,问问是否有夏姓大臣八年前曾在盐政任职。”
陈脊见沈亭山陷入沉思,没有打扰他,而是转向梁宽问道:“大师,这黄柳生是他的真名?”
梁宽不知陈脊为何会问这样的问题,不由一怔,但仍笑着回答道:“那还有假名不成?”
陈脊扭头看向沈亭山,沈亭山登时会意,解释道:“梁叔,黄柳生其人极为神秘,我们遍寻多日都没有任何人见过其真容,或者说,见过他的人都已命丧黄泉。眼下,我们唯一的线索便是曾在丧行见过他写下的字。奇怪的是,我们都不曾见过黄柳生,却对他的字迹非常熟悉。”
梁宽恍然大悟道:“你们是疑心有人借用‘黄柳生’的名号为恶?”
“若是‘借用’,那真正的黄柳生为何到今日都不曾现身,任由他人用其名头行凶?”
梁宽摇摇头道:“这老衲便不得而知了。”
陈脊更加困惑了,“我现在真是一个头两个大,线索明明很多,却始终一团乱麻找不到真正有用的那一条。李执事这个破案的关键究竟人在何处?刘大明明知道当年真相,我们却不能去询问,就算问了他也不会说。哎,眼瞅着马荣捐出来的盐又要吃完了,难不成我们就卡在这了?”
然而沈亭山却不觉得案件卡住了,相反,他心中此刻如拨云见日般晴朗。
“呆子!跟我走!”
陈脊瞬间愣住,“去哪?”
“去了你就知道!”沈亭山着急忙慌地站起身来,仍不忘与梁宽行礼道别,“梁叔,想来你是不会与我们一同离开的吧?”
梁宽闻言一笑,眼底尽是释然:“你们去吧,我要留在这里向佛祖赎罪。”
“可是,黑衣人刺杀不成极有可能去而复返,大师你”
陈脊话还未说话便被沈亭山止住,他向陈脊摇了摇头示意他莫再相劝,而后又转向梁宽,拜道:“大师保重!”
说罢,他便领着陈脊告辞而去。
及至山下,陈脊方问道:“你不怕他丢了性命?”
沈亭山呷了一口酒,笑道:“怕有如何,不怕又如何。有些人有些事,总是不可强求。”
陈脊不解地随沈亭山登上马匹,“好死不如赖活着,从山上捡回一条命,我现在宝贵得紧。”
沈亭山笑道:“是吗,那我倒是要带你去个好地方!”
陈脊好奇道:“这个时辰了还能有甚好地方?”
他说着仰头看向天上弯月,这一番折腾后,眼下已是夤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