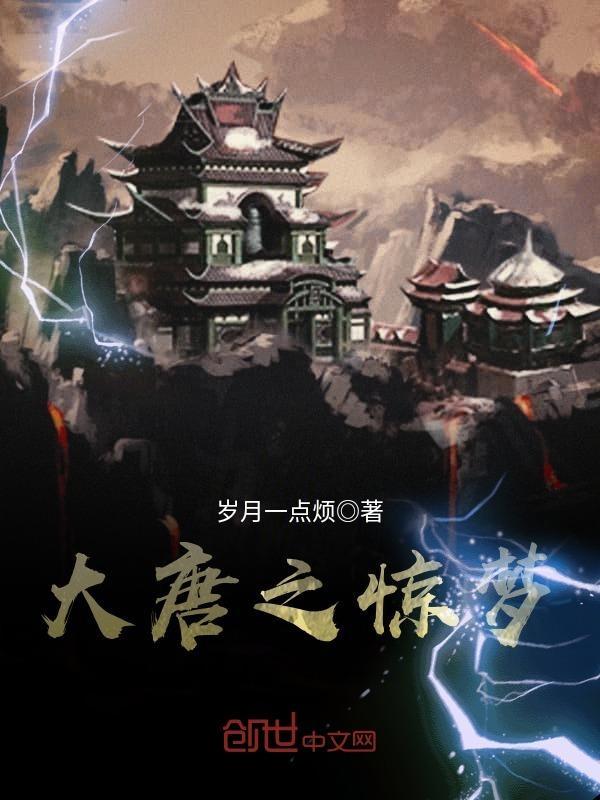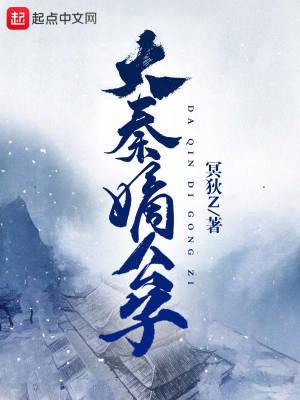笔尖小说网>破落户一朝逆袭之我靠五个儿女扬眉吐气 > 第九十九章 献礼当日(第1页)
第九十九章 献礼当日(第1页)
寿宴当日,天还未亮,百里府邸就已经灯火通明了。百里张庆穿着一身崭新的绛紫色官袍,腰间玉带在烛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他站在书房中央,满意地看着桌上那幅精心装裱的《椿萱并茂图》。
"老爷,画已经检查三遍了,绝对没问题。"管家小心翼翼地捧着画轴,"老奴亲眼看着的。"
百里张庆捋着胡须,眼中闪烁着志得意满的光芒:"好,好!今日太后见了此画,定会大悦。"他伸手轻抚画轴边缘的锦缎,"杨大郎倒是识相,知道借我百里家的势。"
窗外,第一缕晨光穿透云层,照在画轴的玉质别子上,反射出一道冷冽的光。百里张庆没有注意到,这道光恰好映在角落里一个小厮低垂的脸上,照出他嘴角转瞬即逝的冷笑。
"来人,备轿!"百里张庆整了整衣冠,"今日我要第一个入宫献礼!"
朝阳初升,紫禁城的朱红宫门缓缓开启。百里张庆的轿子刚到东华门外,就听见一个清朗的声音:"百里大人今日好早。"
轿帘一掀,只见杨大郎穿着一身青衣布衫站在轿旁,眉目如画,气度不凡。他手中也捧着一个长条形的锦盒,想必是要献的寿礼。
"杨贤侄。"百里张庆勉强挤出一丝笑容,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瞟向对方手中的锦盒,"你今日也来献礼?"
杨大郎恭敬地行了一礼:"不过拙作,不敢与大人相比。"他目光扫过百里张庆随从捧着的画轴,状似无意地问道,"大人今日献的可是那幅《椿萱并茂图》?"
百里张庆下意识地侧身挡住画轴:"正是。杨贤侄献的又是何物?"
"不过是一幅寻常的山水罢了。"杨大郎微微一笑,"太后素来喜欢江南景致,书生便斗胆画了一幅。"
两人正说着,宫门内走出一队太监,为首的正是太后身边得力的李公公:"两位大人来得真早。太后有旨,献礼的大臣和学子先到偏殿候着。"
偏殿内已经聚集了十几位前来献礼的大臣。杨大郎寻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殿内众人。忽然,他瞳孔微缩——柳小侯爷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百里张庆身后不远处,正把玩着一把象牙骨折扇。
"诸位大人稍候,咱家去请太后旨意。"李公公说完便退了出去。
殿内顿时嘈杂起来。杨大郎趁机起身,装作欣赏殿内摆设,慢慢向百里张庆的方向移动。就在他距离百里张庆只有三步之遥时,一个端着茶盘的小太监突然脚下一滑,整盘茶盏朝着百里张庆的方向摔去。
"小心!"杨大郎一个箭步上前,用身体挡住了飞溅的茶水。百里张庆惊得后退两步,手中画轴差点脱手。
"大人恕罪!奴才该死!"小太监跪在地上连连磕头。
百里张庆脸色铁青,正要发作,柳小侯爷忽然从旁边插了进来:"百里大人息怒,今日太后寿辰,不宜见血光。"
他一边说一边用折扇轻轻拍了拍百里张庆的肩膀,"大人的画轴没沾湿吧?"
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柳小侯爷身上时,杨大郎迅速从袖中滑出另一幅尺寸相同的画轴,与百里张庆手中的调换了。整个动作行云流水,不过眨眼之间。
"多谢小侯爷关心。"百里张庆回过神来,检查了一下画轴,"幸好无恙。"
杨大郎与柳小侯爷交换了一个几不可察的眼神,各自退开。没人注意到,杨大郎的袖口多了一道细小的茶渍。
巳时三刻,太后驾临太和殿。百官按品级入殿朝贺。百里张庆作为三品大员,排在献礼队伍的前列。
"臣百里张庆,恭祝太后娘娘千秋圣寿,福寿安康。"百里张庆跪在殿中央,双手捧着画轴高举过头,"臣特献《椿萱并茂图》一幅,愿娘娘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