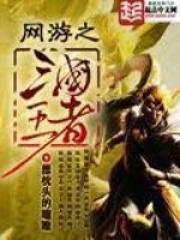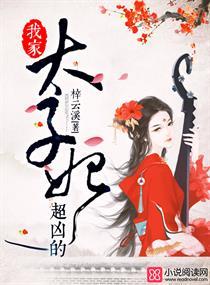笔尖小说网>重启人生,我用金钱碾压一切 > 第九十二章 自治之门系统低温运行(第3页)
第九十二章 自治之门系统低温运行(第3页)
“以前总觉得,系统评分就是高压监控,谁走慢了、谁错了一步都会被扣分。”
“但现在,灰域只是给了一个方向感,像风一样,不推你,也不挡你。”
一位社区志愿者接话:
“是啊,虽然有时候走歪了,但系统只是提示一句‘也许可以这样’,而不是直接贴个标签说‘你错了’。”
秦川坐在角落,听着这些声音,心里生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。
灰域变了。
也许更准确地说,秦川自己也在变。
过去,他以为控制就是保护。
后来,他明白了,理解才是保护。
而现在,他开始学会,放手也是一种理解。
那天下午,他在随身终端打开灰域核心日志,写下一行文字。
“系统不为定义存在,而为允许存在。”
而就在秦川沉浸在这场小型讨论会的氛围中时,江南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。
报告标题是:
《后评分时代社会秩序演化趋势初探》
报告指出:
自灰域系统转向低介入自治模式以来,城市微型社群活跃度上升百分之九点六,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下降百分之四点三,公共资源自主调配效率提升百分之二点八。
更重要的是。
人群在没有强制评分压力的情况下,行为一致性水平并未下降,反而出现了自发优化倾向。
这份报告被称为“自治秩序萌芽信号”。
也标志着灰域真正完成了从系统主导到社会自驱的初步过渡。
那天深夜,秦川独自走在回江南城的路上。
耳边是风声,是远处江面拍打堤岸的声音。
没有系统提示,没有评分预警。
只有这个世界最原初的回响。
他忽然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。
“如果有一天灰域不再被需要了,会是什么感觉?”
不是恐惧。
也不是遗憾。
而是某种近乎释然的平静。
因为从一开始,他就不是为了系统本身而构建灰域。
他是为了让这个世界,在有一天,能不需要它。
那一刻,他在随身终端输入一行新的日志注释。
“系统存在,不是为了证明它有多正确。”
“而是为了在它不再被需要的那一天,依然能骄傲地说——我来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