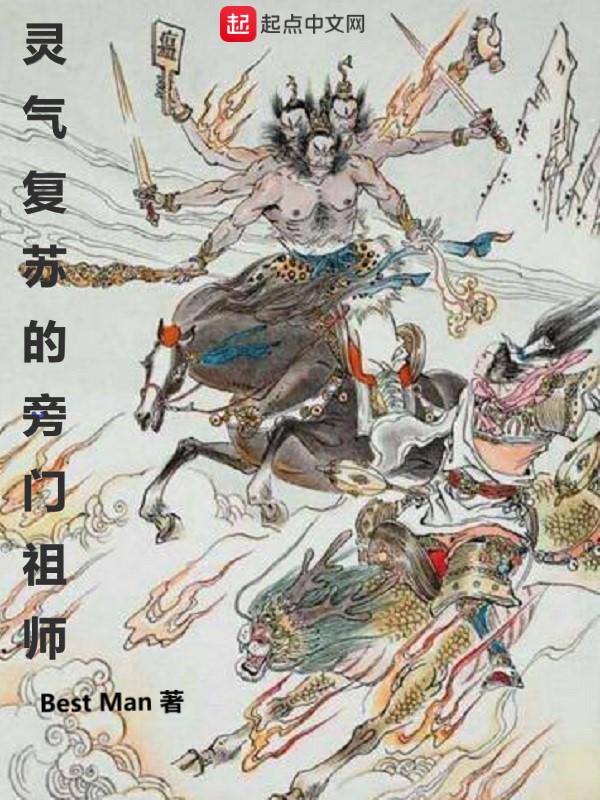笔尖小说网>女尊之渣女难为[快穿] > 7080(第10页)
7080(第10页)
谁也想不到,就在这?一切大好的?当口,平地?遭了一场飞来横祸。
原是要从春兴班这?住处说起?。
王雁芙置办这?小院子,花费可不少。除去先?头交的?四成银钱,余下的?都还欠着银号的?呢。她便将这?所院子的?房契和戏班的?箱笼行头等,作为欠款的?抵押,每个月按照本利相加的?数目,慢慢还着钱。
就在去年底,那银号曝出?了账目亏空,眼看可能要破产。银号大掌柜见势不好,竟然趁年关?之前,卷走了账上所有的?现钱,不知道逃到哪去了。
银号东家报了官,整个正月里都在四处奔走求存。三月时才磕磕绊绊地?转出?了一些债权,换到了一笔周转资金。不料银号危机的?消息不胫而走,储户们为了自?保,在四月里一窝蜂地?涌过?去,把储蓄撤了个干净,让空虚的?银号雪上加霜。
平京城的?初夏,显出?从未有过?的?潮湿和闷热。
五月,资金在各家商号里轮转,富者获其利,贫者受其累。春兴班院子的?房契在其中,就像江洋翻覆时,波涛里挽不住的?小舟,完全?无法自?主。
债权倒了一手又一手,最后落到东昌银号那里。
王雁芙刚得?了消息时,着实松了口气。
平州城里有些门路的?人,都知道东昌银号的?秘密。它明面上的?东家,是李大帅的?六位义女之一,手眼通天的?平京名媛,巩季筠。再背后的?掌控者,据说就是“上头”的?人了。
总之一句话,东昌是不可能像从前那家银号一样,说完蛋就完蛋的?。只要春兴班还能唱戏,就能慢慢还债,日子依然如旧。
不曾想,东昌完全?没有耐心,根本不愿打理这?些散碎的?烂账,也不曾交接账目,就派人前来通知了一声:“东昌银号现要收回这?处房产,你们限期搬出?去吧。”
这?怎么能行!
王雁芙辛苦半辈子,就攒下这?处院子,如今平白无故打了水漂,哪能甘心呢?
她辗转了关?系,托了人去缓颊,想要维持债务,继续还款保住房产。可巩季筠见多了千百大洋的?生意,还真没把这?小院放在心上,听了有这?事?,只当耳边风。
王雁芙只得?秉着一纸诉状,告到平京法院。
这?下,巩季筠终于正眼看了看春兴班。
这?一眼里,究竟有多少恶毒的?意思,春兴班师徒们在此时还是完全?不懂的?。
王雁芙这?官司打得?冤,恰似以卵击石一般。法院袒护豪强,审得?不咸不淡,把她的?诉求接连驳回了两次。有热心的?朋友劝她别再打下去了,她只是拿一口硬气撑着,不愿放弃。
她就是这?么样的?人,总是抱着最好的?希望,预备最坏的?打算。提前把身契还给徒弟们,是为了避免彻底输官司后,连这?一屋子活生生的?人也成了“资产”,就再没有活路可走了。
身契再多,也总算发完了。
王雁芙坐在通铺边上,看着徒弟们发红的?眼睛。
她自?家没有成婚,也没有要孩子。这?些她一手带大的?徒弟,名义上有一纸身契,实则都是她最亲的?儿郎。
世?情?险恶,小儿郎家被催着长大,谁也没有法子。
她稳住心神,尽量柔和地?讲着。
“明儿个又要开庭了。这?是最后一庭,比前两回都要紧。我一早要就出?门,你们好好吃饭,不要闹腾。
“如今你们年纪还小,拿了身契,别急着给出?去。珍惜自?由身,先?搭班一段时间,观察观察班里的?人。若是从上到下都有信用,好相与,再考虑入科深造。
“咱们一定要记得?,搭班就是半个外人,可得?谨言慎行。但也得?手眼勤快,遇上干活的?机会,别叉着手旁观。你们对别人实在,别人才会对你们实在……”
她平时教戏,严厉极了。就阿光来的?这?三四个年头里,眼看她手里藤条换了十多根。遇着徒弟偷懒、性子顽劣不服管教,她手下丝毫不会容情?,“啪”一下打过?去,当时就能鼓出?条血印子。
今晚,她像是把心都掏出?来了。说话的?音调软和极了,憔悴的?脸上带着一点淡淡的?笑,给这?个抹抹泪花,给那个揉揉脑袋,眼神落在每个人面孔上,舍不得?离开。
第二天一上午,阿光都魂不守舍的?,心里总是隐隐约约觉得?,师傅这?次应官司的?事?有古怪。可究竟有什么古怪,他?又说不上来。
他?最近总是想起?,在他?尘封的?模糊记忆里,有谁曾经跟他?说过?这?样的?话:
“有人在操控这?一切……这?世?上之人,都是她的?耳目……”
说话的?人,声音和面孔都不大真切,可它确实在,一直在。奇怪的?是,他?竟追溯不出?这?话到底是哪来的?,是谁和她讲的?,他?又是怎么听到的?。
他?原以为,那是自?己小时候偷听了家里长辈谈论政事?,留下的?印象。可他?如今长大了,有些小时候的?事?已不记得?,唯有这?句话,在岁月的?洗练里,越来越清楚。
尤其是到了这?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?关?口,他?脑海里便有个人在轻声说着:“只要改动一个念头,便可以推翻世?间许多因果?……只能迂回智取。”
奇怪的?是,虽说这?句话没头没尾,却最能让他?冷静。
一旦想起?这?句话,他?就觉得?,自?己还有好多事?情?没来得?及做,那说话的?人对他?怀着唯一的?期待,和他?站在同?一边。
他?就知道,必须振作起?来了。
阿光心思纷杂,在家里待不住了,起?身就往胡同?口去,站在楝树的?浓阴下,往街上盼望。